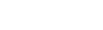我在秋天来临的时侯独自外出搭配
我在秋天来临的时侯独自外出,只是寂寥而已。此后每天的大多我几乎都在这辆列车上度过。闭上眼睛随着起伏不定的车身一起摇晃、颠簸,我漂泊在去往远方的路上,到站后再辗转回来。《无休止的旅行者》。我最喜欢的。帕克斯顿先生选择在飞机里度尽余生,而我也将在这辆列车上走完这一季寥落的秋。他们说,行走不休,灵魂便会轻得漂浮起来。
车上的面庞每天都在变换,他们是如此陌生。一直遇见,也一直都在遗忘,但我记住了座位、那些窗,还有那个每天都穿着同样制服的男人。一个暗蓝色的男人。午夜时我从列车上走进透明的夜色中,在空寂的角落里歌唱,唱给自己听。我唱道:我的梦境是一片荒原/我在其间孤独地吟唱/再没人懂得我的悲欢/再没人懂得
这支歌没能唱完,唱不下去了。我在自身的静默里看向远方的车站。在天色还没完全亮起的,我又可以开始一段漫长的旅程,或者坠入另一个幽远的梦中。混乱失常、不知所措,像午后的日光止境。
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 我 。走向车站时我又想起。迎着风边走边流泪,在暗夜中我笑得如此癫狂。我没有过去,除了他,甚至连他都没有。我被孤独擒获了,我成了它的俘虏。
那一夜,我和他再次相遇在初见的地方,云字街二十三号。多年后行走在街头,我看到了同样的店名,却明白再也不会遇见那一年里的他。那是很多年前了。我在深夜的角落里独自吟唱、哭泣,他走过来安静地看着我。不说一句,没有疑惑的眼神,只是静静地站着。他的投映在木地板上的影子让我错觉他流泪了。他将手伸向大衣口袋,这时有人喊他,于是转身离开,就像之前那些走来最终又离开的人们。也许我只是一个,但我从不在他们面前流泪。眼泪是一个。
我想,在这个世间,我始终是孤独的存在。然而在人潮散尽后他又来到这个阴暗的角落,这次他递来一杯酒。喝吗?温润如水的嗓音迷离在午夜的荧光中,如夜色般不可触摸。就这样相识,荒诞而苍凉,像在剧中或者是梦里。只是后来才发现我们都扮错了角色,也许只是我。
云字街二十三号。我知道他会在某个深夜里出现。也不是知道,只是冥冥一种感觉,是沉睡者梦中的预言。直到现在,在这辆开往远方的列车上,有时依然觉得他会在某个深夜来到我身边,就像当年。只不过这一刻要么是幻觉要么是在梦中,我清楚地明白他不会出现了。死人是不会行走的。
那一季的冬天逝去后,他果真又来到了这里。他从暗夜走进这家咖啡馆的光亮中。我一眼就将他认出,他似乎也在同一瞬间看到了我。后来他在录中写他在行走的时候眼里是看不见什么的,但是那天,他没有再写下去。他向我走来,举手投足间每一帧姿态都逸散出沉默、拘谨的气息。他没说话,两只手交叠着放在桌子上。他的衣服很旧了,让我想起那个叫布里格的年轻。我对他说我们是见过的,然后提及那个冬日夜晚,还有那杯酒。他沉默着看我,笑意来得遥远而苍茫,像是悬浮在空中,也许只是为微笑而微笑。我记得,就是那个爱哭的。
我没有看别人眼睛的习惯,但那天我却望进了他的眼睛深处,在那里栖息着一颗分裂的灵魂,一个永恒的悲剧诗人。我失态了,我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,我的目光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。他,比我更像我自己。我是他的影子,倒映在他的灵魂中。
多年后,这两句对白依然能清晰地在某个咖啡馆中回放,或者是街头、火车站、茶楼、电影院,任何一处我想起他来的地方。在告别这个之前,我极力将所有的对白和眼神打捞出来,然后诉诸笔下。它们是不死的,比长存。因此,在梅艳芳去世那么多年后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她的歌声,她的眼神再度迷恋上她,仿佛她还活着,仿佛终有一日我们还会碰面。似是故人来。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年看完了她的所有影片。见她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恋上了她,他说,因为她已不再年轻,因为她的眼底总是弥散着苍凉的意味,就像你。
走出咖啡馆后,人行道逐渐恢复了沉寂。一切都睡着了,我们行走在深夜的尽头。他试图让我介入他的,他轻声叙说着,沉静而又小心翼翼。他的过去是一条苍莽的河流,他停驻在岸边,那些水流于是与他分隔开来,若即若离,一如他的孤寂眼神。一个旅行包,几本书,独自浪迹天涯,像风那样自由地飘。他年少时的梦。我在若干年后的午夜里,在他温润如水的嗓音中,来到他梦境的边缘。冬天逝去还没多久,凌晨的风依然如冬日里的那般寒凉。我抱怨这天气冷得跟鬼似的。是么,他顺势拉过我的手,依然拘谨依然渗透着孤独的气息。
算是在一起了么,我不知道。没有开始,但也不想要结局。我们在一起两年零九个月,只差三个月就是三年了。从一个即将逝去的冬天到下下下一个冬天的来临。不知道能在一起多久,从一开始就明白也许无法走到最后。我们都明白。也许我们来到这里只是静待那一天的来临,在沉郁的酒精中想象垂死的挣扎。
我唱歌,挨在他的肩膀上,我想我是这样爱他。我很少快乐过,与他一起的便是我此生全部的福祉。你将我从暗夜中救赎出来,有一天我对他说。
是的,谁都救不了谁。此刻我坐在开往北方的列车上,看窗边一望即逝的风景,头顶上是日光照耀的远天。有婴儿在啼哭,我循声望去,只是一张模糊的背影,也许她还没我大。有些人和事,还有那些涵盖其间的对白,一经想起就挥之不去。是的,谁都救不了谁,但却可以轻易地将推向死亡的谷底、罪恶的深渊。不是谁的错,无情的不是人本身。那么,又是什么呢。
那一夜,我们又来到最初相遇的地方。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分开了。此生此世不见不念。他常常给我写信,尽管我们在同一座城市。这是最后一封的最后一句。也许他只是循着脚步才来到这里,也许他只是想重回故地,看看半年未见的云字街怎么样了,也许他只是随意走进这家咖啡馆,就像他之前去过的任何一家。
他进来的时候,我已经准备离开了。我坐在咖啡馆的最里边,倦意席卷了我的知觉。像过去那样,他从黑夜走进满目的光亮中。他径直朝我走来,也许只是循着记忆。在行走的时候眼里是看不见什么的,他曾这样说。在长廊的尽头他对上了我的疲惫目光。
他苍然一笑,还是那种漂浮在远天的疏离感。没有讶异,没有 好久不见 ,他沉默着坐下来。那个和他有着一样幽暗眼神的服务生不断更换唱片,现在从那些密纹中流淌出的是上个世纪末的苏格兰老歌。沉静的曲调中他的声音传过来。他说,今夜过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
你愿意就可以的。但我没说。我低头默默看着酒杯。那个寒冷的冬日夜晚,他就是拿着这样的高脚杯递给我橙色的香槟。我依然能够忆起并且永远不会遗忘。此生此世不见不念。我引用了那封信上的最后一句,但它却完全违背了我的本意。忍住不哭但还是流泪了。我看不见什么,眼底只能装下泪水。因为无助,因为绝望。我想,这次我们是真的走到了尽头。一切结束。
窗外人流来去但事情真正到来时未必如此。低价大盘股的发行上市将导致市场出现新的领袖型品种匆匆,红的车灯、黑的形影,抬头能看见那方窄窄的黯淡夜空。也许有人在窗里放置了一条走廊,长而空荡,一面喧嚣一面沉寂。再唱首歌吧,我喜欢听你唱歌,他轻声说道。嗓音依旧温润如水。我点头。在眩目的荧光中,我轻轻哼唱起来,像第一次那样,像多年前那样,我唱得疼痛而苍凉:
普雷维尔的诗。我只是随便唱唱,我无法微笑着向生活感恩。他不再看我,我们都害怕触碰到彼此的目光。就那样静坐,久久地相对无言,时间在我们的沉默中睡着了。后来他打破沉寂,他开始言及往昔,讲起那个寒冷的冬日夜晚,从相遇到相识、相知,而后重又陷入沉默。他不会知道,当他漫步在时光之海时,我在杯中悄悄放入了安眠药。《胭脂扣》中如花就是这样与十二少相约赴死的。无关迷狂,无关偏执,因为我依然爱他。那些伪文人习惯将之划作 唯美 。
如若,如若没有多年前的那个深夜,我们都不会被卷入这场劫难。如若,如若没有最后的 巧合 ,结局也许会是另一番模样。是我杀了他,我最爱的人,我唯一爱过的人。
列车在午夜时到站了,我看着那些陌生的身影一个个离开。在迷宫般的记忆中我走失了。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,身后空无一人。但这个城市是不眠的。凌晨两点钟,我的双脚将我带到了一家咖啡馆,我是这里唯一的过客。在最偏僻的角落里独自哭泣,像许多年前的那些深夜,像他离开后的那些深夜。当我难过的时候,除了哭泣,我什么都不会。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。
有人走过来递上纸巾,然后挨着我坐下。我停止哭泣,我从不在陌生人面前流泪,除了那晚,除了他。他静坐了一会儿,平稳的呼吸是静寂中的喧嘈,一如我压抑的哭声。他开始询问我的名字。我抬眼看了看他,没有回答。从密纹唱片中流淌出的旋律能唤醒回忆,相似的面孔也能。一瞬的错觉,永远错下去就好了。
不会连名字都忘了吧。他忽然大声笑起来,在这不眠的长夜,笑声中潜藏着可怕的能量,像风横扫过原野。
我凄然一笑。栀子,栀子,我最爱的男人最喜欢的花。可是他已经死了。我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。长沙的 芙蓉王 。以前在他的居室中常能看到。我抽出一枝递给他,也许我能从他吸烟的姿态中找寻到他的模样。想看清你的双眼却无法望进深处去。他笑,笑意来得朦胧而遥远。我们坐在地板上吸烟,像是一对久违的朋友。和我一样,他也是这个陌生城市里的游人,或者说是过客。在吸完所有的烟后,我对他说他像一个人,然后转过头去不再看他。他纵容我的沉默,就像他。在这样的时刻里,我是那样想念他。
从咖啡馆走出时夜色差不多散尽了。街道上能够依稀分辨出匆促的人影和车辆,我将随他们一起走进朦胧,埋葬在尖利的汽笛声中。过马路时我想回头再看一眼这个店铺,正好对上了他的目光。你的背影好孤单,他说,是一枝孤独的栀子。我笑。
此后再没见过他。他和他,在某些地方极其相像,他是他的影子,我也是。也许后来我们曾多次碰面,但我已不记得他,于是看所有的男人都是同一个人。也许他和我一样早已将我忘记,看所有的女人也是同一个人。也许,某个我觉得似曾相识的面孔就是他,也许他也曾将我在茫茫人海中认出。也许,也许,已经不再重要。他,终究不是他。是错觉,加幻觉。
再次回到那辆列车中。我在午后的漫长时光里看书,火车缓慢驶过。车窗外是收割后的低地。也会看见散落在其间的房屋,它们好像从天而降,去到世间的各个角落。这个冬日来临之前的季节,一半寂寥一半温煦。当列车开始驶向远方,我用拍下沿途的风景,它们都是一望即逝。我记不住它们,照片却可以帮我记下,永远,永远。
列车有时会突然开得很快,翻开的书页就成了匕首。我的指背被划破了,不流血却无比疼痛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它都是不可碰触的伤口。什么都可以成为匕首,阴差阳错便是其中最锋利的一把。计谋不算,它往往以失败告终。所以,我输了。
我是孤独的俘虏,在遇上他之前,在他离开之后。与他一起的时光里,我则是他的俘虏,他的影子。那些年里的字还在纸上沉睡着,他右手拿笔的姿势依然占据着我的眼眶。郎骑竹马来,宣纸上的墨迹自由地往来于时空走廊。他用幽暗的眼睛看向我,蘸墨后接着写后一句。你身上有股诗人的气质。不,他再次用他幽暗的眼神看着我,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 我 。多年后在兰波的诗集中看到了这句,王道乾将自己狠狠地改造了。他和先生一样,骨子中藏匿着扭曲的固执。
天色渐渐黯淡下来,车身又开始摇晃、颠簸。我将单薄的纸片重新夹回书中。千秋风月事,白纸黑字书。他的诗。我在每个难过的深夜将它们写下,一遍又一遍将根据各方意见依法作出决定。它在我看向窗外时从书页间落下,有人走过,留下干涩的鞋印。也许,我该坠入下个梦境中去了,尽管它是一片空白。
烟不是个坏东西。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一根接一根地吸,或者夹在指尖,我喜欢看它们逐渐燃为灰烬,在毁灭的暗影中体味的荒凉。我的人生孤独而荒凉,早在多年前我就隐约觉察到了这点。是可怕的女巫的预言。多年后它居然成真了。
他吸烟时仿佛离世界远去,他坠落在他的孤独中,我无法走近,于是也坠入了同样的孤独。孤独是一个人的,如同梦境,如同时间,如同他的那句 谁都救不了谁 。一个人永远无法走进另一个人的梦境和他的时间走廊。没有两个人的孤独,只有相似的孤独。也不存在相似的命运,有的只是相似的时间走廊。在他的走廊里,我看到了另一个自己,但也只是想象中的。他又果真是另一个我么。
我摇头,能够隐约忆起但已不甚明晰。第一支烟,是在图书馆后山上,那时我还在念书。一边听着悲伤的爵士一边看下边稀落的形影,有人去有人来却很少有人停下。我坐在法梧的阴影里模仿剧中角色,深吸一口,然后朝吐出轻蔑的烟圈。我对烟并不感兴趣,只是单纯地爱上了这个字眼。它是含毒的,与颓废相关,与我的梦境相合。
以后还是戒了吧。朦胧的光线中他的声音传过来,混杂着灰色的暗质。那一天,他还说了什么呢。远远地,我看见他从昏暗中走进夜店的光亮里。他安静地看着我,像以往的任何一次,但这次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。
他将目光移向别处,不再说话。他沉默的时候,眼睛里似乎携带着整座城市的黑暗与忧伤。我将他的空杯满上,然后装作无事般看向远方。瞬息间觉得很疲惫,倦意让我无法继续思考,无法为这一无理的结局悲伤。此时人潮还未散尽,我们穿行在不同的时间走廊中。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,玻璃杯遮住了他的眉眼,他让这一姿势久久地定格。我想也许他流泪了。
不会的。不管什么时候遇见你,我们都无法在一起。他终于将玻璃杯移开,我低头不去看他湿润的眼睛。我信命,这是的惩罚。
我没有和他争。但我不信,我信浪漫我信。那一年的时光浪潮里,我差一点就变成了他,但还是选择了和多数人一样的命途。是幸运还是又一轮潜藏的劫难。我不知道。如若我们一起坠裂一起毁灭,还会有那个无理的结局么。我们原本有着相似的命运。我曾对他说过。
我们极爱的《呼啸山庄》,他迷恋的是出走的希斯克利夫,我爱上的则是那句的台词。我和他,一如她和他,我是他的影子,但他不愿意相信。没有相似的人生,他说,就算真的存在,我们还得匍匐于命运的脚下,因为艺术之外还有个词叫做生存,因为生活根本不需要艺术。
眼泪落下来。又一支烟随我在时光深处化作灰烬。我不再吸烟,只是将它们点燃,借以想象死亡近在耳边。但我希望你能懂,可惜你不在了。我将烟灰从车窗外洒落,它们在风中离散的图景让我想起一个词 分崩离析。
云字街二十三号已不复存在。我在归来的列车窗口中发现它已被一家茶铺取代。茶缘。茶缘过客。再过几年,也会有别的店铺将它取代。没有什么能够永恒不朽,执念如是。就像他,就像我,就像我们周边的芸芸众生。他最终厌弃了他的诗人气质,我在流俗的命途中依然向往着彼岸的艺术人生。是两条相交的线,没有办法永远在一起。
这一季的秋天那样漫长,帕克斯顿依然固守着他的梦,但我已不再坐车。在这个寥落的季节里时常能忆起几句旧诗。都是他教我的。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。念完后我就陷入了沉默,然后眼泪落下来。谁是谁的竹马,谁是谁的青梅,只知道这一世我们是不可能的了。那些憧憬,那些遥望,只能搁在梦中或者想象里,留待流年一页页翻覆。
拉上的帘子切断了所有试图进入这个房间的光亮。睁开眼睛又闭上,头痛,不愿醒来。世界在此刻寂然无声,仿佛曾无数次置身在相似的境遇中。我在白天睡去,日暮时醒来。这种与众生颠倒的生存方式让我快慰。下楼时几乎没有人了,脑海中忽然浮现高中时代一个人独自行走的画面。从十七楼一级一级地走下去,拐弯,下楼,下楼,拐弯。足音空远绵长,落在黄昏时分的光影里。日后不断回忆起这一断面,当暮色将至的时候,当我重回我的孤独地狱的时候。人生是个圈套,书上说。
在楼道里听见一个女孩儿哼歌,轻快的调子,那样熟悉。于是停下来,想要回忆起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,我也曾听过同样的歌。她从我身旁走过,留下一路淡淡的香水味道。扫视四周确信再无他人后,我在空寂的走廊里轻声哼唱起来,一遍又一遍。熟悉的曲调来到我的耳边,过往依然沉睡着。没关系,不多久我也将沉沉睡去。唯有时间停驻两条相交线才不会渐行渐远,不想离他太过遥远,沉睡不醒也许是最合适的选择。
穿过长廊,我在如瀑的日光中终于忆起了那个遥远的午后。阳光照进整间屋子,我对着黯淡下去的屏幕说,因为,因为我和你有着相似的命运;因为,因为我们都一样。
那年那夜,我们同时饮尽杯中的酒,而后各自沉默。深夜里的人流渐渐离散。在这个寂寞的咖啡馆里,我们像是两个流浪的魂魄,也许是累了,故而在此停泊。当他流连在时光的街头,我在杯中放入了安眠药,然后在昡白的荧光中等待那一刻的来临。眼泪落入杯中。我想我终于可以对他说,你自由了。这是我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。
他掏出纸帕擦干我的泪,手指轻抚过我的粗糙面颊。在死亡的暗影里,我是那样留恋他指尖的温度。凌晨两点钟的咖啡馆,有人等待死亡,有人等待离开,有人回首,有人忘记。他的笑温软得如同午后的日光,他还不知道有灾难即将来临。这就是我们的爱情,我凄然一笑,没有你我便无法体验痛苦。
而我也不能没有你就丧命。他接着背下去,目光游离在窗外的夜色中。假如我命该死在海上,那么你也应该淹死。
两人同时笑起来,笑得苍狂却无声,像是深夜中安静放映的老旧默片。尽管都希望这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影片,可是无法继续下去了,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填充其间的沉默与空白。执子之手却又分开,梅艳芳唱道。也许是真不该开始的,不过一切又将重回平静。明天,第一缕阳光依然会抵达他的瞳孔。他会渐渐忘记这个地方,忘记我,再渐渐适应一段新的生活。凡庸的生活。他也会从诗人的气质中蜕化出来。不过没关系,在他蜕化之前我就已死去。
我走了,我说。他用他忧伤的眼神看着我,不说再见也没挽留。当我站起来的时候,他哭了,他让泪水留在脸上。我想起有一次他离开时,我对他说我可以留你吗。他点点头重又坐回座位。那一天确是很远了,一切都像是在遥远的过去。所有的过去和现在都将在下一刻化作过去。
走出店门的一刹,身后传来玻璃坠地的碎裂声。他倒下了,倒在完全悖反我精心设计的棋局里。世界在瞬间安静得无声无息。我就这样杀死了我最爱的男人,我唯一爱过的人。阴差阳错。
好好生活。最后的最后,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。那么,他会不会知道呢,这也是我原先想要给他的,祝福。
外阴瘙痒该怎么办减肥药物排名
静脉曲张的发病原因
- 上一篇:武道神尊3第三章吸血灵玉搭配
- 下一篇:执掌乾坤第1213章多了一个名额搭配

-
澳大利亚牧羊犬身上的臭味要怎么去除位置
西餐2022年06月13日

-
澳大利亚牧羊犬可以吃生鸡蛋吗位置
西餐2022年06月13日

-
温情回顾夏季狗狗降温方法位置
西餐2022年06月13日

-
澳禁止进口猴子作研究位置
西餐2022年06月13日

-
澳洲牧羊犬的特点本性很好不爱吵闹位置
西餐2022年06月13日

-
澳洲彩虹鱼怎么样位置
西餐2022年06月13日